

编者按:
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黄州区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宣传普及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作用,在云上黄州APP,黄州声音微博,“今点黄州”微信号、抖音号、视频号等多个新媒体推出《党史百年》专题栏目,重温红色党史、讲述初心故事、回眸历史瞬间,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凝聚“做顶梁柱、当领头雁、建中心城”的精气神,谱写新时代黄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今天编发第七期:《刘少卿对广州起义和参加红军的回忆(二)》
栉风沐雨,风雨兼程
百年传承,红色激荡
庆祝建党100周年
刘少卿对广州起义和参加红军的回忆(二)
攻打银行破营垒,
奉命走险劝敌降。
放火焚烧军械库,
广州起义志凌云。
国民党新军阀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即第四军)的警卫团,是新组成的,有三个营十二个连。其第一营是由第四军的特务营改编的。据说营长是第四军参谋长缪培南的侄子。第二营是由第四军的工兵营改编的。第三营大部分是由省港罢工的工人组成的新兵部队。
第三营有四个连,营部有八个人的传令兵班。营长施述之(海南岛人)、副营长黄烈(广东北部人)、营部中尉霍书记官(广东人)、九连连长(广东人)、十连连长姓赵(湖南人)、十一连连长是个有名的大个子、老李(广东人)、十二连连长(湖南人)。该营除排长以上的军官和营部传令班有盒子炮(即驳壳枪)外,当兵的还未发枪,警卫团团长梁秉枢(广东人)、团参谋长和团指导员(相当团政治处主任)都是湖南人。团部和第三营全部住在八交(音)会馆,第三营营部住在三层楼上,各连住在平房里。第一、二营均住在离八交会馆外较远的地方。

1927年12月10日夜吹了熄灯号后,黄烈副营长和霍书记官将我叫到他们的身边。黄副营长对我说:“今夜传令班不能脱衣服睡觉,你要带个传令兵担任值班,听到有什么动静,或者有什么人上楼来,就即刻向我报告”等等。我遇着这样的交待还是第一次,不知是怎么回事。对于黄副营长严肃的指示,我只是莫名其妙地答应:“是,是,是!”可是内心紧张得怦怦跳。受领任务后,我即召集全班的人传达副营长的命令。大家听了,其精神的紧张与我是一样的,哪里还敢睡觉呢!当夜我带一个传令兵值班,守在楼梯门口,一步也不敢离开。
在漫长的数小时中,我一会儿竖起耳朵听,一会低着头睁大两眼往楼下看,听不出有什么动静,也看不到有什么人上楼来。这时我心里想,也许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吧?老是这样自问自答,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年轻人有点想眯一下眼皮,正在这时,猛然的听到营部办公桌上的大座钟当当当三下响声。啊,是11日凌晨3点钟了。此时,精神上觉得轻松了些,再过一两小时,就要天亮了,大概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发生吧,这样不经心地也不知又过了多少时间,忽然从远处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机枪声!啊呀!我猛然一声叫出来,这就是副营长说的什么动静吧!于是我一面叫值班的传令兵守住楼梯口,一面赶紧去报告副营长。我刚走到副营长的办公室门口时,他已起来开电灯了。我喊:“报告!”他面带笑容地说:“知道了,你快去把营长接回营房来”。他同时叫霍书记官起来,并对他说:“我们党的决议实现了。”我一听到党的决议,就知道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看情况,是要和谁打仗了!我精神振奋地带了一个传令兵去营长的公馆接营长。我刚走到楼梯口时,就发现一个少校军官背着一大捆红带子(作识别记号用的),急急忙忙地上楼来。他对我操着湖南口音问:“你们黄副营长在么?快叫他把这些红带子发到各连去!"他的话音刚落,黄副营长已站在我的后面,高兴地答道:“我在这儿!”他们两人在谈话,我接过红带子放在一边,并立即命令两个传令兵快通知各连派人来领红带子,而我也下楼去接营长。当时我又增加了一点军事上的判断能力,肯定是要打仗了。当我到了施营长的公馆门口时,他已走出门来了,还没有等我向他行礼,他就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我说,是黄副营长叫我来接你的。这时我认定施营长不是共产党员,因为他完全不像黄副营长那样,对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
当我们和施营长回到离营门不远的地方时,就发现了团参谋长和第十连连长被打死在营门外的广场上。这时我和传令兵莫名其妙地互相瞪了一眼,同时又看到团指导员站在高台子上,向上百的人讲演,大声地说:“这些反动派,我们一定要消灭他们……”我们这才明白,死了的那两个家伙是反动派。当时团指导员所讲的,就是像我在家乡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那样,对那些土豪、劣绅和反动派,就是要用革命的暴力对待他们,把他们彻底打倒。
当我们和营长走进营房大院时,我看到全营人员脖上都系着鲜红的带子,在电灯光照下,显得特别鲜艳夺目。又看到了那个送红带子的少校军官和黃副营长在向各连的排以上军官训话。当施营长向本营走近时,黄副营长发出了立正的口令,向他报告整队的情况。紧接着施营长率领全营到广西会馆,就在八交会馆旁边,该处原来是武器库,领取枪支弹药。这时我看到那个送红带子的少校军官,胸有成竹,干练果断,处理紧急事务,比起别的军官特别活跃、忙碌,似乎就是他决定和指挥这个营的一切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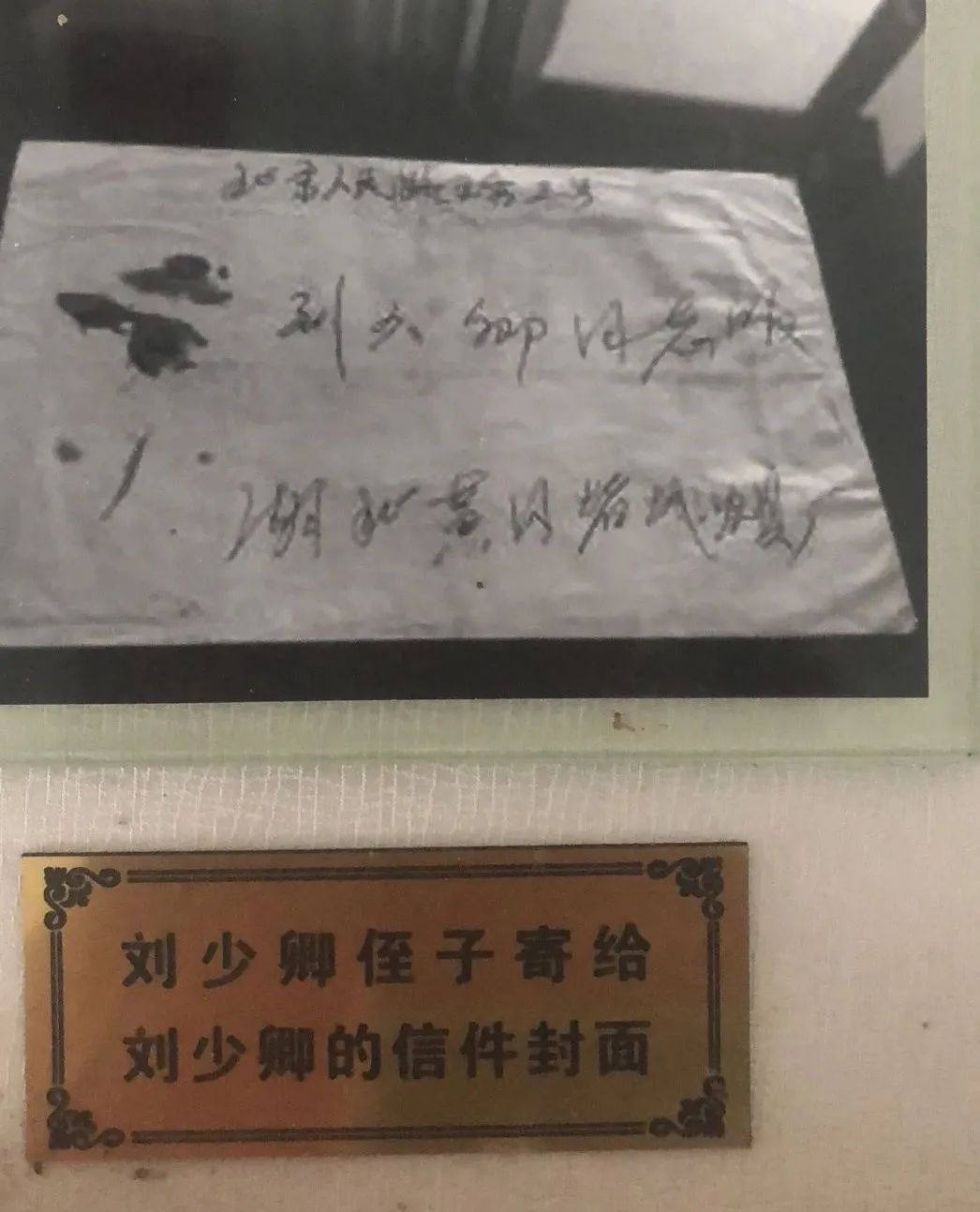
当部队完成了领取武器任务以后,天快破晓了。梁秉枢团长率领第三营全部,向位于珠江边(天字马路与永汉马路口)的中央银行反动派第四军军部进发。中央银行房屋是钢筋水泥砌成的,门都是钢铁铸的,比一般的建筑坚固得多。加之又有反动派的精锐部队把守,房星顶台上堆着大量的沙包作为防御工事。当起义军接近中央银行时,立即展开向守敌进行猛扑。守敌就从顶台上用机枪、步枪向起义军以密集的火力进行射击。起义军虽然受到了些伤亡,但进攻的锐气有增无减,一次比一次冲得猛烈,一连冲了近十次之多。当战斗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珠江里帝国主义的军舰,不时地向起义军示威,支援守敌。守敌凭借着坚固的房屋为防御阵地负隅顽抗,居高临下向我起义军射击。而我进攻部队又只能利用永江马路一侧的房屋作隐蔽,向敌仰射,其效果是不大的,给敌人的伤亡也是很小的。加之我起义部队都是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新兵,根本没有爬楼、攻坚、巷战的工具和本领。就这样激战了两个小时之久。太阳从东方出来老高了,部队没有吃饭,确实有些疲乏,进攻就自然地停下来了。
梁团长和军官们正在议论着什么,突然传来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就好了,我们的炮兵队来了,“吊拉马海”的(广东骂人的方言),用大炮轰他反动派的。在旧军队里称炮兵是军中之胆。所有参战的官兵们正在兴奋时,果然高大的骡马,拉着大炮急驶过来了,此时,大家长时间热烈鼓掌,迎接我们的炮兵队参战,接着炮兵队摆开了阵势,架好了炮,用排炮向中央银行守敌进行猛烈的轰击,轰了半小时之久,虽然把守敌的气焰压下去了,对我军进攻的士气大大提高了,但是步兵仍然冲不破守敌的坚固房屋阵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于是梁团长对第三营另作新的战斗部署,令施营长率九、十一连去攻打住永汉马路一个死胡同里反动派第四军十二师的军械股(即我在那里当勤务兵的单位),令黄副营长率十、十二连仍在原地坚持战斗。这时支援的炮兵队也陆续离开了阵地。
我带着三个传令兵,跟着施营长去攻打反动派十二师的军械股。这个军械股所库存的军火,主要是机、步枪、迫击炮和弹药,有一个监护排(该排都是两湖的人)。军械股的主任姓陈,是个少校(广东人),有三个股员是尉官。这个胡同是个丁字形的死胡同,只有一条路进出,像个闷葫芦似的。当我军一接近胡同口时,敌人就从胡同口里边向外射出机关枪子弹来,幸好,我们没有伤亡。这时施营长察看了胡同的房屋、地形,并对敌情作了分析后,对两上尉连长说:“要进攻这个军械股,完全是个巷战,显然我们部队没有这个经验,采取硬攻硬拼,不仅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也无希望取得胜利。要争取这个战斗的胜利,必须把军事进攻和劝降结合起来。军械股的陈主任,既是我的同乡,又是我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在进攻之前,让我写个信给他,劝他缴枪投诚,两个连长看他说的好像很有把握,就同意了。营长知道我在这个军械股当过勤务兵,他写好信后令我送进去,我拿着信站在胡同口大声高呼监护排的人(该排每个人我都认识),我对他们招手喊,“我是刘少卿,奉施营长之命,送信给陈主任,请你们千万不要开枪,快去禀报陈主任,准我进去。”
大约过了十分钟,监护排的排长就喊:“刘少卿,陈主任同意你把施营长的信送进来。来吧,不要怕,两军交战,不杀来使!"施营长听了这席话笑起来了,并对我说:“你快把信送进去,如果陈主任要问你的话,你说是叶总司令在胡同(巷)外边,不问就不要说什么,要他回信,快去快回。”于是我高兴极了,觉得这项任务是很光荣的,就快步走进去,走进胡同里边时,监护排长就来接我,并问:“外边是怎么回事儿”(可见他们的消息是闭塞的)?我说:“我们施营长给陈主任写的信,等会儿他会告诉你的。”当我上楼把信递给陈主任时,他拆信一看,就皱起眉头来了,恼起了那可怕的鬼脸,像挖了他的祖坟一样,狠狠地瞪了我几眼,并将信撕个粉碎,又用手抓住我颈上的红带子,使劲地拽了两下,险些没有把我勒死!他骂道:“吊拉马海的,你这做面样用的(广东话)"?我说:“这是打仗做识别记号用的"。他一听,气急败坏地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地问:“外边是什么人指挥打仗"?我说:“听说是叶总司令”。他突然在我面前停下来又问:“是哪个叶总司令,是叶剑英,还是叶挺?”我说“不知道是哪个叶总司令"。他一听就板起鬼脸,举起拳头要打我,还是那个讲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陈中尉,急忙过来把他的拳头拉开说:“你打他有什么用,他是个塞郎(广东人称小孩为塞郎哥)",懂得什么,你不给施述之回信,叫他走就算了嘛"!在这紧张的时刻,我想,这是好来不好回去的,可是经陈中尉这么一说,我心里轻松了一大截。这时陈主任这条恶狼猛地把我往楼梯口一推说“你给我滚”!险些被他推得滚下楼来。接着监护排长用不安的神态,送我往外走,可又突然听到那条恶狼在楼上喊:“刘少卿,'吊拉马海的’,你不要再来了,你若再来我就枪毙了你!”我仰头向楼上一望,这家伏确实显出一张杀人脸色,难看极了。我也没有理他,就加快步伐,辞别监护排长和老朋友们,回来向施营长汇报了。他一听,火了,要求调炮兵来轰!不一会儿来了几个炮兵军官察看情况,他们说:“一没有地方架炮,二是炮弹打不着目标,一打就要打坏一批商店和居民的房屋”。总之,炮兵发挥不了作用。因此,施营长对两个连长说,现在只好与守敌对峙,等到黄昏以后再说吧。
部队一整天没有吃过正餐饭,只是永汉马路的各商店,从楼上吊下来些水和饼干给我们吃,大家疲乏不堪,在马路上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太阳快落山了,两个连长把我叫醒,问施营长上那去了?我猛地爬起来在附近找了一遍,没有找着,不见营长,这下我就慌了,此刻十一连连长请九连连长把队伍招呼好,自己到团部去请示。团部也不知道施营长哪儿去了。于是团长就决定那个背红带子的少校军官来代理营长。
代理营长一来,迅速了解了敌情和附近居民民的情况,想了想之后对两个连长说:“不能硬攻,赶紧收集火油、干柴等易燃物和沙包地,准备晚上用火攻,非把这股敌人消灭不可!” 大家一听,豁然开朗,说这个代营长真行,有办法,消灭这股敌人有把握了!火攻的工具和沙包很快准备好了,时间已到黄昏,就派出了少数人利用居民的房量作隐蔽,前进到胡同里边,尔后把沙包逐渐推进到敌人的近处,以沙包作掩体。不多时,沙包垒起有两米多高,厚度也有两三米。这下好了,敌人的机枪火力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敌人的视线也完全被挡住了。在沙包的后面,我们运进了十多桶火油,大批的干柴和其它的易燃物。然后以沙包作掩体、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敌人的射击。把易燃物抛到敌人近处。此后敌人简直像瓮中之鳖,袋中之鼠,一切自由权、主动权都操在我们的手中了。
12月12日凌晨一时许,代营长给两个连长下命令,准备点火攻击!这时十一连连长建议再等一个小时,他说:“为了防止敌人在火势一起从居民的房屋打通逃跑之路,此时只留一个排的兵力就够,其余五个排插到敌人驻地左右后方去,以歼灭乘机逃跑之敌。”代营长同意了这个部署。约在凌晨二时半,代营长令我带两个传令兵,从沙包掩体的两侧,越过沙包去点火;我们三个人冲上去,同时把火点着了。真是干柴遇着烈火,顿时火光冲天,迅速蔓延。敌人慌乱了,大喊:"快灭火啊!"你想他哪里来得及扑火呢,又哪里扑灭得了呢!到了四时左右,听到守敌军火库各种弹药的爆炸声,震撼了天地,烈火的光焰,照亮了军火库周围的永汉马路和天字马路……
12日天刚破晓,两个连长均来报告,果然不出十一连李连长所料,守敌一见我们放火时,一面派少数人灭火,一面把主要力量打通居民房屋逃跑,可是未能得逞,守敌监护排全部破俘。军械股三个股员均未看见,估计是藏在老百姓家里未找出来。那条恶狼似的陈主任,则被大火烧死了,只剩下一副肠肚未成灰。大家骂他:“这个顽国不化的反动派,应得这个死有余辜的下场!”
代营长带领我们打扫战场之后,把部队集中在永汉马路,他带我回团部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原来黄副营长攻打中央银行的战斗已停止,他带着十、十二两个连又去攻打驻文德马路的反动派十二师司令部留守处去了。代营长要我给九、十一两个连长送信。信上说:“九、十一两个连由九连长负责指挥,即刻带到文德马路去与黄副营长会合,他自己随后就到。九、十一连正在向文德马路行进时,又接到团部的命令,说情况紧急,你们不要去与黄副营长会合,直接把部队带到省财政厅门前待命。部队于黄昏前到达了省财政厅门口席地就坐,这时听见观音山方向有激烈的步机枪声,并看到山上有人走动。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希望能参加观音山的战斗,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贡献自自己的力量。可是等了许久,也不见上级下命令,也不见代营长和黄副营长以及十、十二连来,也不知文德马路的敌人消灭了没有。人们这些盼望和关心,是为了广州起义第一次参加战斗,要求杀敌立功的积极表现。
这两个连又整天没有吃饭,在万分疲乏的情况下,大家躺在地上还老想着参加观音山的战斗;夜深了,还能听见观音山上激烈的枪声,不时也能看到观音山方面升起的信号弹,但也判断不出这些信号是谁打出来的。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两个连长集合了队伍,大家精神抖擞起来,以为是到观音山去参加战斗哩!可是九连连长讲了话:“我们现在要出发了,要往乡下夜行军了,要求大家不要说话和咳嗽,不要落伍掉队……。”大家也辨不出东南西北,行军行了一整夜还辨不出方向。天亮了,还在继续走,走到铁路上了,有人说这就是广九铁路,前面不远有个镇子,就是石龙。部队既没有进石龙镇,也没有在铁路边停下,而是绕道向另一个方向行动。当部队行军又不知走了多少路,发现了一个山洼里有两三百人的队伍,一问话,他们也是参加广州起义的,昨夜从广州市撤出,刚到这个地方休息。这两支队伍汇合一起,足够五百来人。这时九连连长也不知上哪去了,只有十一连大个子李连长领导我们,他和这个队伍的几个军官商量之后,两股队伍继续行军,走有二十里地,进入到一个桔子园里,大家是又饿又渴,只好搞些桔子吃,充饥解渴。大约在一个小时后,部队继续行军,走了十余里地,进到一个山冲里,就发现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有人向我们打枪,他们都是着便衣的,除有些步枪外,大部分人都是持梭标和大刀。他们一面向我们打枪,一面从山上冲下来。并喊道:“我们是民军,你们把枪弹给我们留下,放你们一条活路,如若不然,你们的性命难保!”我们这两股队伍,大都是外省人,既不会说广东话,也不懂广东话,突然遇到敌人这种严重威胁的情况,于是阵脚大乱,无人指挥,大部分的人丢枪说跑,谁也管不住谁。部队完全溃散了。我和三个传令兵及营部的小勤务兵共五个人,始终团结在一起。五个人有四支驳壳枪,乘大乱之时钻进了密林里,躲藏起来了。黄昏时,我们几个人商量着究竟往哪里去,几支短枪怎么办?有人说把枪的壳子丢掉把枪插在裤腰带子里,有的人说,那不行,带着枪走总是有危险的,商量了一段时间,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说:“还是把枪都丢在草丛里,你是班长带着我们往山外边走就是了。”我一听到大家那么一说,心里砰砰跳,心中完全无数,确实也想不出办法往哪儿走好。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好!已经黄昏了,你们把枪丢在草丛里,跟我走吧"!
就这样我带大伙盲目地走出密林外,也不知东南西北,没有目标一个劲儿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完全是听天由命。忍受着饥饿和疲劳,不知越过了多少山川河沟,走了多少里路,也不知深夜几时,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火光,再一听有狗叫声。啊!前面是个村庄,我小声地对大家说,不要掉队。我和大家毫无顾虑地往村庄里走去,刚走到村庄口,就有十来个人(都是青、中年者),手持梭镖、大刀,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只见他们态度还算和善。他们问:“你们都不是广东人吧,要回广州市去吗?今夜太晚了,就在这里住下,明天再赶路行吗?”我们几个人一听,觉得有理,不约而同地互相瞟了一眼,回答说:“好吧,谢谢你们的好意”!于是,他们把我们带进一 个青砖小炮楼里,走时,将炮楼门锁上了。我们一看,互相细声地说:“糟了,住进了黑店,今夜有危险”。另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传令兵老练地说:“管他的,天要下雨,阎王要命,你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办法的,几天几夜没睡,好好地睡下吧,到明天再说。”可是,我老不放心地说:“就这样被黑店里做了肉包子,未免有些太冤枉了。”那老练的传令兵又说:“人死如灯灭嘛!我们被他们弄死了,是包包子还是包馄饨,由他去,他们吃了会拉肚子,也是报应,我们死而无罪,赶快睡觉吧!"(另一个传令兵插话说:“你倒很干脆啊!” )他这么一说,倒使大家的紧张情绪轻松多,逗得那个勤务兵哈哈大笑,大家也跟着笑起来了。
待大家睡着了,我从门缝里往外看,发现有两个年轻人各拿着明晃晃的大刀,把守着炮楼门口。我根本睡不着,心里盘算着:我们几个人如何活着跑出去。如果黑店里的人一开门,我们就一起冲出去,必要时和他们斗打,夺过一大刀,持刀自卫,只要逃出这个村庄就好办了。我打好主意把他们几个人推醒,要他们轮流地从门缝向外看,监视那两个持大刀的人。并把我拟好的计划,细声地告诉了他们。他们都说行,到时候再说吧。
雄鸡叫了。我们一听鸡叫,快天亮了!天一亮我们就该启程赶路了。事情哪由得我们来做主呢?正想到这里,不料黑店的人不声不响地推开了门,有的提着马灯、有的提纸灯笼、还有拿着手电筒,把炮楼门堵塞得严严的。前面进来了两个中年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摸啊!搜啊(我身上还有二元纸币放在毛线衣口袋里,他们用手捏毛线衣,没有捏出来是钱),什么也没有搜着。于是那两中年人就问:“你们的枪呢?’’我们四个人同声地说:“都是当勤务兵的,没有枪。”那个老练的传令兵说:“我是当伙夫的,没有拿过枪”。这两个中年人没有捞到什么油水就往外走,他们刚跨过门槛时,其中一个人突然转过身来,朝我的脚上狠狠地盯了几眼,接着蹲下来解我的鞋带子,并把我推倒在地上,脱我的鞋袜,这时我才明白,他看中了我(在广州起义前购买的脚上穿的陈嘉庚蓝球胶鞋,我只好光着脚跑步了。黑店的人走后,仍旧把炮楼门锁上了,我们的计划也落空了。天亮了,太阳刚露出头,黑店的人来了,打开炮楼的门说:“你们现在可以走了。”并用手指着说:“广州、沙河就朝那个方向走"。我们几个人连连向他们点头道谢,按照他们指的方向,离开了这个黑店似的炮楼,往广州方向奔走。(未完待续……)
责编:区融媒体中心 童益



